



作者:侯少林 时间:2021/11/16 15:13:17 浏览:2972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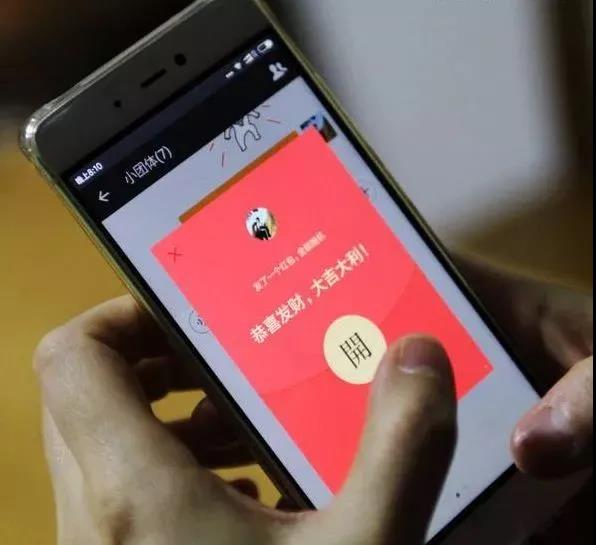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山东沂水县法院通报一起微信群抢防疫捐款红包案件,判处被告人李某犯盗窃罪,罚金2400元。2020年1月31日,李某通过扫描微信好友在朋友圈内分享的“某高校校友情”微信群二维码,加入该群。李某在明知该群内红包系由专人接收并用于购买抗疫捐赠物资的情况下,当日抢了2个红包,共计300元。群成员发现后,要求李某退还红包,李某拒不退还而后退出该群。随后,李某再次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该群,并抢了5个红包,共计900元。
该通报的警示意义在于,微信群不是法外之地,微信群内的红包不能随意领取。抢红包前,理当先判明该红包是供群友娱乐随便抢的红包,还是具有专门归属的红包,如果是专属红包,就不能伸手领取。
从该判决出发,可以分析盗窃罪适用的一些问题。
一、抢专属微信红包属于盗窃行为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盗窃”一词的理解。
长久以来,传统的刑法观点认为,盗窃必须是秘密的取走他人所有的财物。现在刑法界强有力的观点认为,盗窃不要求秘密这一要素存在,只要是违背他人意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把他人的财物取走交给他人或者为自己占有的,就是盗窃。也就是说,即使所有权人在场,把财物取走的行为,也可能属于盗窃。
不要求盗窃具有秘密要件的观点具有合理性。首先,这样的行为在社会中可能比较常见。如果犯罪分子用强力把财物夺走,可以由抢劫罪或者抢夺罪进行处理,但是趁人稍不注意或者来不及阻止的情形下,将财物公开地“带”走的,犯罪人没有实施其他强制行为的,不能认定为抢夺或者抢劫罪。如果不由盗窃罪进行规制,可能就会出现处罚的真空地带。再者,既然趁主人不在场秘密将财物取走属于盗窃罪,从逻辑上来说,在所有权人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的,行为更加恶劣。从严重性的角度来说,更应认为属于盗窃行为。因此,在法律上,这样的观点没有问题。
诚然,对“盗窃”的理解,要注意社会大众的主观认识。一方面,刑法规范是治理社会的重要一环。而这一任务的具体承担者是具备刑法知识的司法工作人员,刑事律师也要在案件的办理中与司法人员一道,通过争论明晰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包含律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以自己的理解运用法律,办理案件。另一方面,刑法规范要由全体社会成员来遵守。为了实现实质的守法,必须让社会成员知晓法律的禁止界限。不能要求社会成员遵守其认为属于不被法律禁止的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然违背他人意志,拿走其所有的财物的,当然也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这样的认识并没有异议。至于,盗窃行为属于刑法的哪一条的规定,规定的具体细节是什么,属于违法性认识更深入的范畴,不能认为可以阻却认定盗窃犯罪的成立。
综上,在微信群里公然抢专属他人的红包的,属于具备盗窃性质的行为。是否应构成犯罪,还应结合具体的法律规定做出认定,详见下文分析。
二、抢专属他人的微信红包,属于什么类型的盗窃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的行为类型分为五种。
第一,数额型的盗窃犯罪。刑法对此的规定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第二,多次盗窃,是指2年内3次及以上盗窃。
第三,入户盗窃。户是以生活居住为核心认定的,是指,供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入户盗窃,就是进入户中实施盗窃行为。
第四,携带凶器盗窃。凶器,是指国家明令禁止的管制刀具等,或者虽然是生活中所用,但是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比如菜刀。
第五,扒窃,指的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盗窃行为。
沂水县法院通报的本案例,笔者倾向于认为属于第一种的数额型盗窃犯罪。
首先,并不构成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本案例发生在网络空间,明显的是,李某并未入户盗窃,也并未携带凶器盗窃。
其次,多次盗窃类型对应的事实难以查清,是否属于多次盗窃类型需要结合事实做出判断。
李某第一次进入微信群领取了2个红包,第二次进入微信群领取了5个红包。对此,存在疑问的事实问题是:究竟按照李某进群的次数,认为李某盗窃次数为2次,还是按照盗取红包的数量,认为李某的盗窃行为数量是7个。
如果李某进入微信群内后,在短时间内连续抢红包,那么虽然所抢红包的数量超过1次,但是只能认为李某只有1次的盗窃行为。那么李某进入群聊一次,就是盗窃1次,本案中李某的盗窃次数为2次。此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属于盗窃次数达到3次,也就不能认为构成多次盗窃的盗窃类型。如果李某,在进入微信群后,每次抢红包的时间间隔较长,那么每一次的抢红包动作,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多次盗窃行为中的一次行为?对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刑法理论与生活经验做出判断。
生活中的很多“偷”并不是刑法所言的盗窃行为。例如,某人在超市或者菜市场等处小偷小摸的行为,不能认为属于刑法上的盗窃;偷拿他人价值较大的外卖,有观点认为其属盗窃行为,也并不恰当。因为,刑法并不处理生活琐事,“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小偷小摸的行为所带来的物质损失,完全可以当场令行为者予以赔付;道德范围的谴责,也足以令行为者受到“惩罚”。虽然,外卖被偷拿人的报应情绪要求对偷外卖者处以重罚,从客观上来说,被拿走的外卖也价值较大,但是刑法仍然不应将属于生活常理认定为不属盗窃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综上,李某的行为值得刑法处理。从估算来说,张某每次领取红包的数额较大,并且窃取的对象为明显具备财物属性的微信红包。如果其每一次点击抢红包的行为之间时间间隔也较长,可以被认为属于多次盗窃行为。当然,这样的判断,应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案情为依据。
再次,不构成扒窃型盗窃。扒窃行为有两大认定点: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发生场合;盗取的对象为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
微信群属于公共空间。一般认为,公共空间应具备现实性,网络上的多人场所,不应被认为是公共空间。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网络呈现形式的迭代,加之网络的公开性确实对某些犯罪的受害人而言,提高了伤害程度。例如,通过直播侮辱他人的,其比在现实中的公共场所侮辱带给被害人的伤害可能更重。文字的含义应在新的受众那里被重新发现。公共空间的含义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刑法需要对之结合实质解释、扩大解释的方法,将微信群解读为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
已发出的微信红包不属于随身携带的财物。微信红包的发出者,随身携带的是手机。手机搭载的网络账户与被发出的红包存在一定联系(红包过时不领会被退回)。因此,可以看出,微信红包并不是发出者的随身携带财物,两者之间的距离过远。从微信红包的应然接受者角度看,其尚未领受红包,并将其置于自己占有的范围,是否与其成随身关系,答案明显。
综上,李某虽然在公共空间盗窃,盗窃对象却不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其行为不是扒窃。
最后,构成数额型盗窃犯罪情形中较为特殊的类型。
纯粹按照盗窃的数额划分,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按照最高法、最高检的全国性规定是1000-3000元。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进一步规定,山东的单纯以数额入罪的标准为2000元,如果附带有规定的情节,数额标准可以减半至1000元。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全国性规定,盗取救济款物等的,入罪标准数额减半。因此,李某所盗取红包款项具备“购买抗疫捐赠物资”的特殊用途,属于救济款物的范畴,且总计金额为1200元,达到盗窃数额的入罪标准。
三、本案例可以宣告无罪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吗?
事实是评判犯罪与刑罚的基础。本案中,李某盗窃所得1200元;盗窃发生在疫情期间,盗窃的款物属于购买抗疫捐赠物资用途;盗窃途中表示拒不退还所盗款物。因此,虽然欠款数额不是很大,但是情节比较严重。至于影响本案处断的退赃、认罪悔罪、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均不能看出是否存在。
刑事规范中有为轻微罪行出罪或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路径。刑法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司法解释中有,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赔退赃,具有法定从宽情节或者未分赃、分赃少、不是主犯的或者获得被害人谅解条件之一,并且属于情节轻微的,可以由检察院不提起公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规定。
因此,虽然李某罪中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在疫情的当下也颇具警示意义,但是,如果具有罪后的相关情节,或许可以获得一定的宽大处理。

四、公开通报该案例是否合适?
据笔者观察,此案例情况因公开报道与流传,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宣传面,成为比较大的新闻热点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利用李某进行普法宣传的不良观感出现,然而,本案例的通报并非如此。
山东沂水县法院通报此判决的初衷在于刑法上的一般预防。通过公开判例,将其中包含的不法行为公之于众,可以起到对社会成员的警示、引导作用,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守法意识,也有助于刑法的含义通过判决的形式为普通公众所熟知。这种做法的益处非常深远。
与之相关的是,为了震慑、预防未来发生的犯罪,从而提高对当下犯罪人的刑罚量的做法。这其实是将具体的犯罪人作为警示教育的手段,是对人的一种物化,这已被现代的刑法理念、刑法实践所摒弃。沂水法院并非将李某手段化,而是公布案件的来龙去脉,实际是在进行刑事方面的普法宣传,值得提倡。
结语
刑法通过限制自由的严厉手段保护自由。严厉表现在,刑法规定了最为严重的惩罚手段。对自由的限制与保护,此消彼长,两者之间的博弈问题,是刑法人热衷的话题。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网络上,都应注意遵守刑法规则,这也是一种必为的公民义务。